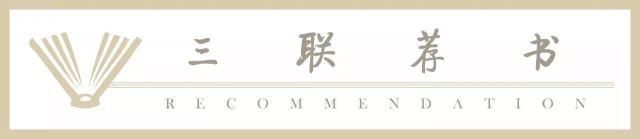阅读量98
有价值的书总会一版再版,被阅读者一再介绍分享。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出版的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已经是这本书在国内的第四个版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英]A.J.P.泰勒 著 潘人杰 朱立人 黄鹂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出版 138.00元 16开/512页/精装 带护封/内文80克纯质纸 之前有过1991年的华师大版、1992年的商务版、2013年辞书社版。我们在网络上也很容易翻到关于它的新近评论。在2024年新版出版前,依然有读者在豆瓣上写阅读这本书之前版本的短评。分享该书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中也很容易搜到。 左图来自豆瓣,上图来自微信公众号。 出版即引发激烈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61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就引发了争论风暴。许多学者群起而攻之: 轻率武断,扰乱人心,作者根本算不得一位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另一些学者则热情推崇: 一部难得的杰作,堪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麦考莱《英国史》相媲美。《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称这部书是“泰勒最完美的艺术作品,一个恰如其分、言语高超、见地洞彻的奇迹。” 唇枪舌剑,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开始,由英国打到美国,不仅在专业书刊和学术讲坛上交锋,还很快扩展到一般大众媒介以至家庭内部,因之朋友反目,父子龃龉之事也时有所闻。 媒体评价 独树一帜、鞭辟入里……一旦通彻领会了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谁也无法再以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这段历史了。 ——《星期日电讯报》 本书运用令人赞叹不已的修正派史学手法,综合体现了泰勒喜用似非而是、激发争议、独出心裁的议论进行阐证的治学之道。 ——《泰晤士报》 泰勒一生始终是一位持异议者……他改变了诸多重大争论话题的依据和立场。 ——本杰明·皮姆洛特,《金融时报》 近代历史学家中最值得拜读、最具怀疑精神、最为原创大胆的一位……整本书既让人信服,又同样令人惊奇。 ——迈克尔·富特,《论坛报》 一部杰作:明晰易懂、富有同情之心、文笔精美。 ——《新政治家》杂志 泰勒可能是英语世界最具争议、无疑也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身为多产的畅销作家、有天赋的记者、自成一格的电视明星,他试图改变对他所处时代的史识。 ——《泰晤士报》 一部几近完美无瑕的杰作。 ——《观察家报》 20世纪所有史学家里其著述可读性最强的一位。 ——尼尔·弗格森,《星期日电讯报》 赞美是热情的,批评也非常尖锐。有批评者直言,作者在为希特勒翻案。 A.J.P.泰勒究竟在这本书里说了什么? A.J.P.泰勒究竟在这本书里说了什么?为何这本书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让我们回到二战后的史学界。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当时的普遍认为是由希特勒按照预定的计划蓄意策动的。这是二战后十多年中占主流的“正统学派”的权威性解释。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和纽伦堡审判中的重要罪证“霍斯巴赫备忘录”都是证据。 在泰勒看来,把罪责推到希特勒身上,不过是一种在战前就已经提出在战后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的解释。原来主张对德强硬政策的人当然满意,因为它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原来倡导绥靖政策的人也能接受,因为要不是希特勒这个疯子,绥靖本来会是一项明智和成功的政策;更主要的是德国人也觉得称心,因为它既然证明一切都坏在希特勒,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了。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解释。 但是泰勒研究现有的记录之后发现,“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无辜的”。他要叙述的将是“一篇没有英雄主角,或许甚至也没有反派角色的故事”。 泰勒用传统的历史写作方法按照时间顺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幕幕话剧重新排演了一遍。他的结论是,希特勒既没有策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弱的同义词;这场战争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事与愿违的忙中出错;“二战”其实是“一战”的继续和重演。 在泰勒的笔下,希特勒既不是神昏智乱(至少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之前)的疯子,也不是严格按计划行事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神经坚强的机会主义赌棍。通常认为是希特勒侵略蓝图的《我的奋斗》不过是多少年来在维也纳咖啡座和德国啤酒馆里随时可闻的陈词滥调的混乱回声。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侵略罪证并普遍认为是希特勒侵略计划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也大有疑问(这部分我们后文会详细解释)。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国会纵火案,进军维也纳兼并奥地利,制造捷克紧张局势以及最后占领布拉格等等,也并非希特勒事先策划、精心操作的结果,更多的倒是一些二流人物或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主动行为所触发的即兴反应,希特勒只是抓住了他们所提供的机会。总之,“他远不想要战争,而且是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部胜利果实;由于别人的愚钝,他差点获得这种果实”。 不仅对希特勒的行状不同常论,对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物都有一幅大异其趣的画像。二战后传统观念里因绥靖政策受到批评的张伯伦既不愚蠢也不懦弱,倒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策得到他的保守党和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跟通常认为或其本人自我标榜的相反,艾登并不是反绥靖主义者,丘吉尔也不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他曾经赞美过墨索里尼,对佛朗哥的事业怀有善意。被普遍推崇为爱好和平的“善良德国人”施特雷泽曼却原来跟希特勒一样怀有统治东欧的梦想。墨索里尼乃是一个爱虚荣胡吹牛皮的家伙,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斯大林也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坚持意识形态教义,一心策动世界革命,倒是个欧洲最保守的政治家,要求维护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安排,并期望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 泰勒几乎把两次大战之间的全部欧洲国际关系史弄了个头足倒立,里外反转。特别是对希特勒的评价,让他遭到集中和猛烈的抨击。 然而,泰勒认为,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持超然的态度,其任务只是“去理解发生过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而“不是去辩白或谴责”。他说:“从希特勒上台的那天起,我就是反绥靖主义政策论者;如果处在同样的局势下,无疑我还会是。但这同写历史不相干。” 对于本书出版后的攻击和批评,泰勒很少搭理,直到1963年本书再版,泰勒以一篇《再思考》为前言作出正式抗辩。他说:“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毫不犹豫,即使他的著作帮助和安慰了女王的敌人,乃至人类的共同敌人。” 以上两部分内容参考了潘人杰先生的《正统与异端》(1993年)《西方史学界关于二战起源的论争述评》(1986年)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也收录在2024年6月上海三联书店新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内。 A.J.P.泰勒的意义和魅力 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在西方史学界所激起的争论已经平息,但泰勒敢于向正统和权威挑战的独立学术精神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他因之被视为“知识界的牛虻”。有人认为泰勒的个性和遭际很像萧伯纳,“才华横溢,学问渊博,机智诙谐,固执己见,离经叛道,惹人讨厌,不可忍受而又无法摆脱,不时冒犯他的史学同行却总是有教于他们”。 而对大众读者来说,泰勒的作品非常具有可读性,他的写作技巧融合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公众写作的流畅性,能够将复杂的历史分析以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给广泛的读者群体。泰勒的写作常常展现出机智和讽刺,加之其新颖的视角和对传统的挑战,非常具有吸引力。读者即便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也无疑会从中受到很多启迪。 书摘 A.J.P.泰勒对“霍斯巴赫备忘录”重要性的质疑 泰勒的观点虽然具有争议性,但他的论证是在已有史实和常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对“霍斯巴赫备忘录”重要性的质疑尤其精彩,下面节选关于这个内容的两段论证,和读者一起体会泰勒的治学方法和文字魅力。 我上了霍斯巴赫备忘录的当。我虽然怀疑它是否像多数作者所理解的那样重要,但我仍然认为它必定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作者都对它如此重视。我错了;而那些批评我的人,他们回溯到1936年是对的,虽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们就使霍斯巴赫备忘录不足信了。我最好在质疑那份某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官方记录”的东西这件事上走得再远一点。论点是技术性的,在一般读者看来也许无关紧要。不过学者们通常正确地重视这种技术细节。按现代惯例,一项官方记录要求三件事。第一,秘书必须与会,先做笔记,会后整理成文。其次,他的记录草稿必须提交参与者校正和认可。最后,记录必须存放在官方档案中。关于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这三件事一件也没有做到,除霍斯巴赫出席了这次会议外。他没做任何笔记。五天后,他根据回忆写出了一份描述会议的普通书写稿。他两次试图把手稿拿给希特勒看,但希特勒回答说他太忙碌,没有时间看它。这种对待据认为是他的“遗嘱”的态度,是出奇地轻率的。勃洛姆堡也许看过手稿一眼。其他人并不知道有这份手稿。它上面的唯一确实的凭证乃是霍斯巴赫本人的签名。还有一个人看过手稿:参谋总长贝克,在德国将领中他对希特勒的思想最为怀疑。1937年11月12日他对希特勒的论点写了一份抗辩;这个抗辩后来被说成是德国人“抵抗运动”的开端。甚至有人认为,霍斯巴赫撰写备忘录是为了诱发抗辩。 这些说法不过是推测罢了。当时谁也不重视那次会议。霍斯巴赫过后不久就离开了参谋部。他的手稿连同其他零散文件一起存档,被人遗忘了。1943年,一位德国军官基希巴赫伯爵仔细阅读了档案,并为军史部门抄了该手稿。战后,美国人发现基希巴赫的抄本,又抄了一份供在纽伦堡起诉之用。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认为,这个抄件比原抄本短。尤其是据基希巴赫说,原抄本包含纽赖特、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对希特勒论据的批评——这些批评现在已被剔除了。也许美国人“编辑”了文件;也许基希巴赫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试图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希特勒身上。现在没有办法去辨别。霍斯巴赫的原件和基希巴赫的抄本都已失踪。幸存下来的不过是一份抄件,也许是从一份不可靠的草稿缩短的,也许是用这份草稿“编辑”的。它包含希特勒在他的许多公开讲话中同样用过的主题:需要生存空间,以及他确信其他国家会反对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它没有包含行动命令,除想要增加军备外。即使在纽伦堡,拿出霍斯巴赫备忘录也不是为了证明希特勒的战争罪行。那被认为是无需证明的。它以其最后经过炮制的形式所“证明”的是:纽伦堡的那些被告——戈林、雷德尔和纽赖特——曾抱无动于衷的态度,并同意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为了证明被告有罪,非得假定计划是带侵略性的。那些相信政治审讯中证据的人,可能继续引用霍斯巴赫备忘录。他们也应告诫他们的读者(因为例如《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的编辑们就没有这样做): 这份绝非“官方记录”的备忘录,是一块非常烫手的山芋。 (《前言 再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5-16页。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出版) 关于“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论述在本书第七章还有一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分水岭的宽度正好是两年。前一次大战于1936年3月7日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时告终;后一次大战于1938年3月13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开始。从那时起,变化和动荡几乎没有间断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大国的代表于1945年7月在波茨坦举行会议为止。是谁掀起这场风暴和开始推动事件发展的?公认的回答是明明白白的: 那就是希特勒。他如此行动的时刻也是大家公认的: 那就是1937年11月5日。我们掌握了那天他讲话的记录。这份文件叫“霍斯巴赫备忘录”,它是依照记录者的名字取名的。人们认为这份记录暴露了希特勒的计划。在纽伦堡审讯中把它大派用场;《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的编辑们则说“它提供了1937—1938年德国外交政策的梗概”。因此它值得详细考察。也许我们会在其中找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也许我们只会找到一则传奇的来源。 那天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者有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外交部长纽赖特,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希特勒的讲话占了会议大部分内容。他一开始就对德国需要生存空间进行全面的阐述。至于将在什么地方找到生存空间,他没有具体说明——也许在欧洲,不过他也讨论了从殖民地获利。但是必须有所获利才行。“德国必须向那两个为仇恨驱使的对手英国和法国算账……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手段来解决,这绝不会没有附带的风险”。将来什么时候和怎样动用武力?希特勒讨论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在1943—1945年期间”。在这个时期之后,形势只会变得每况愈下,1943年应该是行动的时机。第二种情况是法国发生内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对捷克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就来到了”。第三种情况是法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这种情况可能在1938年出现;而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这些“情况”没有一个成为事实;所以这三种情况显然没有提供德国政策的蓝图。希特勒也没有详细论述它们。他接着证明德国无需打一场大战就能达到它的目的;在他看来,“武力”显然是指战争威胁,而未必是战争本身。西方大国太受牵制,过分胆怯,以致不会进行干预。“英国几乎可以肯定,甚至法国也可能,已经把捷克人勾销了,并承认这样的事实: 这个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由德国来加以解决”。没有别的大国会进行干预。“波兰——俄国在它的背后——将几乎不想同胜利的德国作战”。俄国将受到日本的牵制。 希特勒的讲解大部分是白日做梦,与现实生活中随后发生的事风马牛不相及。即使真有所指,它也不是要求采取行动的号召,无论如何不是要求采取大战行动的号召;它是在证明没有必要进行大战。尽管对1943—1945年做了初步讨论,它实际的核心是考察1938年和平取胜的可能性,那时法国会把心思用在别处。希特勒讲话的听众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三军将领坚持认为法国军队比德国军队占优势,即使此外还和意大利交战。纽赖特怀疑法国和意大利是否会即将在地中海发生冲突。希特勒对这些怀疑充耳不闻,他“深信英国不会参加,所以他不相信法国可能会对德国采取交战行动”。从这个杂乱无章的阐述中只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希特勒是把宝押在命运的某种意外转折上,他是在打赌这种意外转折将会给他带来外交上的成功,正像一个奇迹使他在1933年当上了总理一样。在这里,不存在具体的计划,不存在对1937和1938年德国政策的指令。或者即使有指令的话,那就是等待事态自行发展。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这个问题在纽伦堡审判时没有人问及;历史学家们尚未问过这个问题。然而可以肯定,历史学的一个起码规矩,就是不仅要问一份文件的内容是什么,而且要问它为什么会产生。1937年11月5日会议是一次奇怪的集会。只有戈林是纳粹党人。其他的人都是老派保守派,他们仍然身居要职,是为了控制希特勒;除雷德尔外,他们都将在三个月内被解职。希特勒知道,除戈林外,他们都是他的反对者;他也不怎么信任戈林。他为什么向他不信任的而且不久要解职的人泄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容易的回答: 他并没有泄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外交政策中没有任何危机足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或广泛的决定。这次会议是国内事务中的一次运作。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沙赫特的财政天才能使重整军备和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但此时沙赫特在进一步扩大军备计划上却踌躇不前。希特勒害怕沙赫特,而且无法对他的财政论据作出辩解。他只知道这些论据是错误的;纳粹政权无法放松其势头。希特勒想要把沙赫特同其他保守派隔离开来;所以他必须争取他们赞成一项增加军备的计划。他那一番地缘政治讲解没有别的目的。这一点霍斯巴赫备忘录本身就提供了证据。备忘录最后一段写道:“会议的第二部分涉及军备问题”。毋庸置疑,这才是召开会议的理由。 与会者自己得出了这个结论。希特勒离开会议之后,雷德尔抱怨德国海军今后若干年没有力量面对战争。勃洛姆堡和戈林把他拉到墙角,在那里解释说,会议的唯一目的是催促弗立契要求一项更大的军备方案。纽赖特当时没有发表意见。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他几天之后完全了解了希特勒的邪恶意图,接着便经受了“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心脏病发作一事首次于1945年透露出来,当时纽赖特正作为战犯受审讯;1937年或后来若干年里,他都不曾有过健康欠佳的迹象。弗立契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坚持认为德国军队一定不得面临对法国发动战争的危险,并于11月9日将这份备忘录交给希特勒。希特勒回答说,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危险,总之弗立契要更加努力以加速重整军备,而不要涉足政治问题。尽管受到了这样的阻碍,希特勒的策略还是得逞了: 从此以后,弗立契、勃洛姆堡和雷德尔便不赞成沙赫特的财政顾虑了。参加11月5日会议的人当中谁也没有再想到它有其他什么含义,直到戈林看见这份记录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来作为他有战争罪行的证据来控告他为止。从这时起,它一直困扰着历史研究的多个重要领域。它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没有任何东西再可发现的看法的基础。据称,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就对战争作出决定,并对战争作了详细计划。然而,霍斯巴赫备忘录并不包含此类计划,而且如果不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大讲它包含这样的计划,也绝不会有人作如是设想。备忘录告诉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即希特勒(和所有其他的德国政治家一样)打算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它还告诉我们: 他推测这可能会怎样发生。他的推测是错误的。这些推测与1939年实际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提供赛马情报的人,要是只达到希特勒的精确度,是不会为他的客户带来好处的。 (《第七章 德奥合并:奥地利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81-184页。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出版) 附:目录 本书相比前几个版本,内容更加详尽。 图说二战起源 前言 再思考 第一章 被遗忘的问题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第三章 战后的十年 第四章 凡尔赛体系的终结 第五章 阿比西尼亚事件和洛迦诺的终结 第六章 半武装的和平,1936—1938年 第七章 德奥合并:奥地利不复存在 第八章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第九章 六个月的和平 第十章 神经战 第十一章 为了但泽的战争 参考文献 索引 给美国读者写的前言 附录一 潘人杰:西方史学界关于二战起源的论争述评(1986年) 附录二 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比较研究(1986年) 附录三 时代、格局和人——关于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1989年) 附录四 中译本第一版译者的话(1991年) 附录五 潘人杰:正统与异端(1993年) 附录六 郑逸文:等待“泰勒”(1993年) 附录七 潘人杰:调整一下思路和视角(1998年) 附录八 中译本第二版译后记(2013年)